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
“梁庄三部曲”最后一部《梁庄十年》出版后,作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鸿已有多时没有在读者面前露面。直到本月,《收获》杂志首发她的长篇非虚构新作《要有光》。
“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?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。但这个主题,好几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,我一直在调查、访问、写作,直到最近半个月才感到自己慢慢放松下来。”在朵云书院·旗舰店举办的新作分享会上,梁鸿形容“这是一个像山一样的任务”,直到放松下来,她才意识到过去几年自己的压力有多大。
 《要有光》分享会在朵云书院·旗舰店举办
《要有光》分享会在朵云书院·旗舰店举办
压力来自何处?是她接触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少年和一个个家庭的真实故事。《收获》编辑部如此概括《要有光》:其写作基于梁鸿多年的田野工作,涵盖全国各地城乡数十个家庭的深入访谈与跟踪观察,聚焦青少年由家庭创伤和学业压力等外在因素造成的厌学、轻生、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,采取“非虚构+观察+亲历对话”的复合型写作方式,与全社会一起探讨求解之道。
“中国经济越来越发达,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生病的越来越多?我自己虽然博士毕业,好像懂很多知识,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,同样迷茫、痛苦。我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是错位的。我是作家,又是母亲,对孩子细微的震颤非常敏感,所以我开始想写一部作品,我想要看一看这个时代,在家庭内部、在孩子身上,到底发生了什么?”梁鸿自认为是行动派,一旦决定下来,就会往下走。近三年时间,她全情投入,去了不同规模的都市、县城、农村,有的采访在补习班进行,有的走进家庭,甚至有的就在精神病院里。梁鸿说:“我关注的重心首先是孩子,孩子个人的故事。我想知道,在他们身上,究竟发生了什么?”
 《要有光》分享会在朵云书院·旗舰店举办。施晨露摄
《要有光》分享会在朵云书院·旗舰店举办。施晨露摄
书里的第一个人物是敏敏,13岁开始不上学,直到16岁,闭门不出。梁鸿认识这个孩子时,她开始自学,试图考高中。“她和我讲她的故事,逃学、家暴、自残、自闭……后来,随着接触的孩子越来越多,我才发现,敏敏不是个案。”梁鸿坦言,面对这些孩子的故事,她有过崩溃的时候,不知如何下笔,几番斗争,还是想写,“我想,我要对那些孩子负责,当他们面对我的时候,他们的眼神如此真挚。如果我不写,就是对这种真挚的背叛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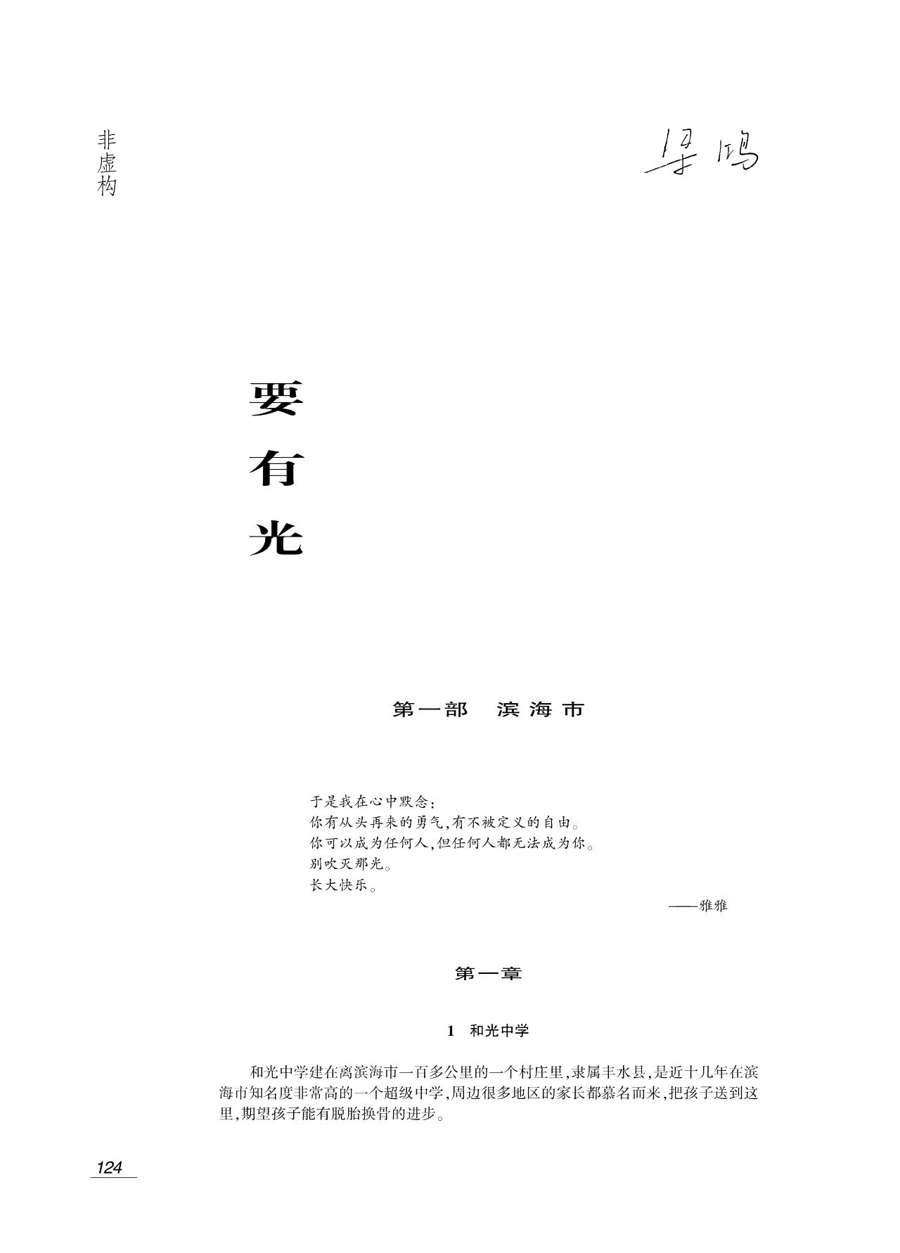 《要有光》在《收获》杂志首发
《要有光》在《收获》杂志首发
因为相处的时间久,梁鸿和这些少年成了朋友。他们带着她去自己的家里,不愿意对亲人说的话,愿意跟梁鸿说。很多家长也袒露了家庭中最深的矛盾,挖出内心深处的痛苦和私隐。“这是我最终坚持下来的重要的原因。有这样一群家长、这样一群孩子,他们在寻找种种方法,试图获得一种新的希望、新的生命状态。最终,我完成了《要有光》这部作品,也许在书里我没有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,但如果你读了它,能够震动心灵一刹那——‘是不是我之前做得不太好?’‘是不是在这个地方错过了孩子?’……这就够了。这就是我写这部作品最大的诉求,触发读者重新审视和孩子的关系、和世界的关系、你和自我的关系。”
“读《要有光》就像坐过山车,有些部分读得非常沉重,这是多年没有过的阅读体验。”作家孙甘露是这部作品的早期读者之一,新作分享会上,他“严肃”地向读者建议去读一读这部“严肃”的作品,“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涉及中国当下千家万户的生存状态、家庭伦理,教育、升学,当代人对自己人生的设想——现在,所有人好像都要有一种不许失败的人生,这种诉求恰恰造成了大量失败者,这是令人痛苦也令人困惑的现象。”
 孙甘露
孙甘露
在孙甘露看来,教育问题派生出很多有意思的现象,比如,大部分家庭的教育职责由母亲承担,父亲是缺位的,既要教育又要陪伴的母亲有时还要面临自己的职业问题,承受着极大的压力。“这部作品的三个部分选取了三个不同角度,第一部分是学生,以孩子的视角为主,第二部分切换到母亲的角度,第三部分是医生与病患。在中国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社会群落,面临着不同的处境,一开始看起来是简单的青少年问题,逐渐引向家长的问题,再深入又是社会问题、女性问题,一个人的职业生涯、家庭关系的复合问题,也包括学校、教师和青少年的关系,都不是简单的。”
窒息感和庆幸感,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谢斌读完《要有光》的两个感受。“为什么窒息?书里介绍了一群孩子和家长,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是更多孩子和家长。这本书里的主人公到最后多多少少走出来或在逐步向好的过程中,在我们的门诊里,还有很多没走出来的孩子和家庭。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,却没有办法提供解法,令人窒息。庆幸的是,无论是书里的人还是现实中遇到的孩子和家庭,社会方方面面,身处这个时代的人都在努力,哪怕像蚂蚁搬家、愚公移山,但终有一天会见到光。我对这一点是非常乐观的。说不定今天书里这群孩子,若干年后回过头看他们成长中经历的最为痛苦黑暗的时候,他们发现自己最终还是安然度过了这个阶段,活得好好的。”
谢斌提及,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安娜·弗洛伊德说过,想要青少年时期正常的这个想法本身就不正常,因为青少年本来是暴风骤雨的阶段。“每一个年代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阶段会经历不一样的暴风骤雨,今天大家谈论的是心理健康,是焦虑症、抑郁症。从专业角度来说,关心青少年心理健康没错,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我们是不是关注得有些过头,反而带来更多压力?”
 谢斌
谢斌
“一方面,中国的家长对青少年心理问题似乎一无所知,另一方面,知识碎片又非常多,短视频带来各种各样的信息。所以,家长非常迷茫,看似懂了很多知识,实际上又什么都不懂。”梁鸿说,书里的小丽妈在小丽不上学之后去学了催眠,参加过很多心理学课程,也做过沙盘,她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改善和孩子的关系,结果全失败了,她的孩子说,“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”。“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错过了孩子?不是我们不努力,不是我们不爱孩子,我们的爱和孩子的爱之间是怎么擦肩而过的,这是最大的问题。文学的任务就在于要把这些事件和关系背后的肌理,最复杂之处的可能性和摇晃的地方写出来。”
 梁鸿
梁鸿
“我们常常说父母和孩子之间要学会表达爱、表达理解,我一边读这部作品一边想,这些属于感受的部分,把它们说出来的效果不一定就是对的。等你的人生过了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,在某个不经意的场合,忽然想起谁对你说过的一句话,到那时才真正理解了他对你的关心。”孙甘露说,这是他在《要有光》读到的另一重感受,“不少细微之处在中国当代文学虚构作品中是没有触碰过的”。
 读者现场提问交流
读者现场提问交流
“我不是心理学家,也不是精神科专家,我在书中更多是用追问和疑问的方式去写的。”梁鸿说。在《要有光》后记里,她写道:“我想到阿叔说‘你就把这句话写出来,一定让大家看到’,想到雅雅说‘如果我的事情被大家看到,或许能给他们一个信心’,想到几个成人因为娟娟的病情吵得一塌糊涂,想到和敏敏在长长的海岸线边的散步,想到吴用眼中闪烁的泪光,想到李风努力寻找词语的瞬间,内心充满无限感动。这些都是神圣的时刻,是生命中因为互相理解、互相关注而有光亮的时刻。那是人类的希望所在。这部作品想写给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每一个人。我内心充满感谢。我希望经由这部作品,重新打量我们自身。不管你有没有孩子,不管你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,不管你家里有没有一个‘生病’的孩子,在看完这本书之后,你要思考,到底是哪些东西让我们的孩子‘生病’了。或者,我们返回自身,思考是我们哪个地方生病了。我希望孩子们读到这本作品,看到其他孩子和你有着相似的经历,但是,他们在努力,努力走出泥淖,努力去感受春天,感受生命中每一丝光亮。他们在努力。我们大家都在努力。”
创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